首页 > 医疗资讯/ 正文
胆汁淤积性肝病(CLD)是一种由胆汁生成、分泌或排泄功能障碍引发的病理综合征,其特征为肝内外胆管系统破坏引发胆汁流动力学异常及毒性胆汁酸蓄积,疾病谱涵盖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等自身免疫性胆管病。尽管CLD早期症状较为隐匿,仅表现为ALP和GGT水平升高,但进行性肝纤维化可导致肝硬化及其并发症,如门静脉高压(PH)、慢性肝衰竭等,最终需进行肝移植。值得注意的是,PSC等免疫介导性肝病在欧洲已成为肝移植的第三大指征,数量超过丙型肝炎,这一趋势充分凸显CLD临床管理的重要性。
1CLD的分类与特征
1.1 疾病谱系
PBC以进行性、非化脓性炎症及小胆管破坏为特征,全球发病率和患病率分别为1.761/10万和14.6/10万,且存在显著的地区和时间差异。患者中约90%为女性,确诊年龄多集中于50~60岁,在儿童中极为罕见。除常规血清ALP、GGT和胆红素升高外,抗线粒体抗体(AMA)对PBC具有高度特异性,95%以上患者可检测到AMA阳性,这使得大多数患者无需肝活检即可确诊PBC。PBC的病理进展可通过Ludwig分期系统进行评估:第1期表现为门静脉区炎症;第2期炎症扩展至门静脉周围区域;第3期出现间隔纤维化;第4期则发展为肝硬化。对于已进展至肝硬化的患者,若不进行干预,其中位生存期(从诊断至接受肝移植或死亡)通常为6~10年。
PSC的标准定义为通过磁共振胰胆管造影或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在胆管造影中检测到大胆管的纤维化狭窄。与PBC不同,PSC多见于中年男性,发病率为1/10万~1.5/10万,患病率为6/10万~16/10万。少数患者(5%~10%)表现为小胆管PSC,另有一小部分患者(约5%)患有与自身免疫性肝炎(AIH)重叠的PSC,这在儿科患者中更常见。通常将PSC视为炎症性肠病(IBD)的肠外表现,肠道微生物群-胆汁酸轴被认为是CLD相关肝纤维化的关键驱动机制。多项横断面研究报道PSC患者微生物群组成改变,其中肠球菌(Enterococcus)的富集是最为一致且显著的表现,其丰度与ALP水平正相关。但令人意外的是,Gui等通过构建IBD-PSC小鼠模型,发现肠道炎症和屏障受损可改善急性胆汁淤积性肝损伤,并减少慢性结肠炎模型中的肝纤维化。这一研究揭示由结肠炎触发的抑制CLD的保护性机制,可能为PSC的多器官治疗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1.2 胆汁淤积的级联反应
胆管细胞增殖,又称为“胆管反应(DR)”,是胆管细胞在胆汁淤积状态下为增加胆汁排出而启动的一种适应性反应。研究表明,增殖的胆管细胞可表达多种抗凋亡基因、趋化因子及促纤维化刺激因子等。在疾病早期,DR可能有助于胆道损伤的修复和消退;然而,在持续炎症刺激下,DR可能进一步导致胆道纤维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诱发恶性转化。鉴于胆管细胞增殖与纤维化之间的密切关联,DR被广泛认为是“门静脉纤维化的起搏器”。
细胞衰老是一种特殊的病理生理状态,其特征为细胞周期停滞、凋亡抵抗以及衰老相关分泌表型。胆汁酸是诱导细胞衰老的重要因子。胆管细胞衰老被认为是CLD进展的关键致病机制之一。与健康人群相比,PBC和PSC患者胆管细胞中衰老标志物p21和p16的表达显著升高。此外,有研究表明,胆管细胞衰老可直接促进胆管周围的纤维炎症反应,从而加剧损伤并阻碍肝再生。在胆管结扎(BDL)、Abcb4-/-等多种胆汁淤积小鼠模型中,均观察到胆管细胞衰老标志物的表达增加。
CLD的核心是胆管炎。胆汁酸毒性不仅取决于其浓度,还与疏水性水平和偶联状态密切相关。其中疏水性胆汁酸具有显著促炎特性。胆汁酸的亲水性如下:牛磺酸结合型>甘氨酸结合型>游离型(ω-鼠胆酸>β-鼠胆酸>猪胆酸>α-鼠胆酸>熊去氧胆酸(UDCA)>猪脱氧胆酸>胆酸>鹅脱氧胆酸>脱氧胆酸>石胆酸)。炎症是慢性肝病的基本病理特征之一,同时也是肝纤维化发生和发展的重要促成因素。
2PH形成的多维度机制
2.1 血流动力学改变
PH发生遵循“阻力增加-高动力循环”双机制模型。近年研究表明,胆汁酸可能通过其血管活性作用参与PH的病理生理过程。一项来自捷克的研究纳入21例肝硬化合并PH的患者,通过分析个体胆汁酸的血清浓度与肝静脉压力梯度的相关性,发现牛磺鹅去氧胆酸的血清水平对临床显著PH表现出极强的预测能力,其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超过0.9。牛磺石胆酸是一种由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生的重要次级胆汁酸。研究表明,牛磺石胆酸可通过结合主要表达于肝窦内皮细胞的G蛋白偶联胆汁酸受体5(TGR5),调节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的活性,从而促进肝内一氧化氮释放,并抑制内皮素-1信号传导,最终降低肝内血管阻力。然而,次级胆汁酸对PH的影响仍存在争议。例如石胆酸是一种非结合胆汁酸,可通过增强内皮素-1介导的肝星状细胞(HSC)活化,加剧肝纤维化并增加门静脉压力。尽管不同次级胆汁酸在PH的病理生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各异,但识别和表征具有潜在益处的次级胆汁酸,有望深化对PH病理生理机制的理解,并为开发新的治疗靶点提供参考。
2.2 CLD特异性驱动因素
肝肾心退行性纤维化是一种新近被识别的纤毛病,由Devane等于2022年首次报道。该病以进行性退行性肝纤维化、纤维囊性肾病和肥厚型心肌病为特征,与TULP3基因突变密切相关。患者早期常表现为肝功能异常,尤其是胆汁淤积标志物显著升高。最突出的临床特征为严重的非肝硬化性PH,影像学检查可见肝脾肿大、肝实质不均匀及PH相关征象。肝组织病理学表现多样,但以门管区纤维化为主,通常伴有极少量炎症细胞浸润和中度非特异性胆管反应。
近期,Wu等通过整合空间增强分辨率组学(Stereo-seq)和单细胞转录组学(scRNA-seq)技术,揭示胆管细胞在胆汁淤积区域的损伤和修复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尤其在门静脉周围损伤修复相关的信号传导中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分析表明,胆管细胞可能作为信号枢纽,整合门静脉区域微环境中的细胞相互作用,从而调控局部损伤修复反应。这一发现不仅深化了对CLD分子机制的理解,也为探索其与PH发生发展之间的潜在关联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3靶向治疗策略进展
3.1 病因治疗突破
UDCA是一种亲水性胆汁酸,目前作为PBC的一线治疗方案,标准剂量为13~15 mg·kg-1·d-1。尽管UDCA已被广泛用于PSC的治疗,但其临床获益仍存在争议。一项长期、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给予PSC患者高剂量UDCA(28~30 mg·kg-1·d-1)治疗,结果显示,虽然UDCA组的血清ALP水平显著降低,但患者达到主要终点事件(包括肝硬化、静脉曲张、胆管癌、肝移植或死亡)的比例升高(26% vs 39%,风险比为2.3,P<0.001)。这一结果主要归因于早期PSC患者或血清总胆红素水平正常的患者出现PH相关并发症。去甲熊去氧胆酸是UDCA的侧链缩短同源物,能够显著诱导富含碳酸氢盐的胆汁分泌,并具有抗炎、抗增殖和抗纤维化特性。由于其治疗PSC的潜在前景,目前正在进行3期临床试验(NCT03872921)。
法尼醇X受体(FXR)是细胞内主要的胆汁酸受体,也是胆汁酸稳态的关键调节因子,已成为CLD的重要治疗靶点。奥贝胆酸(OCA)是一种强效的选择性FXR激动剂,能够减少胆汁酸在肝脏中的积累并抑制细胞凋亡,同时还具有免疫调节和抗纤维化的潜力。然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21年禁止其用于伴有晚期肝硬化的PBC患者,随后在2024年12月指出在无肝硬化的PBC患者中使用OCA治疗时观察到严重肝损伤。这使OCA的临床应用受到限制,并引发对其安全性的广泛关注。EDP-305是一种新型FXR激动剂,能够在大鼠BDL模型中减缓纤维化进展,并已完成2期临床试验。
苯扎贝特是一种泛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PAR)激动剂。阿根廷的一项研究对31例接受苯扎贝特联合UDCA治疗的PBC患者进行了基线和5年随访的配对肝活检,结果显示48%的患者实现了纤维化消退。此外,肝硬化患者的比例从基线时的19%降至5年时的3%(P<0.001)。Seladelpar是一种选择性PPAR-δ激动剂,能够减少胆汁酸合成、抑制炎性细胞因子、抑制HSC增殖和活化,并发挥其他重要的代谢作用。Elafibranor是一种双重PPAR-α/δ激动剂,除PPAR-δ激动剂的作用外,PPAR-α的激活还能通过上调多药耐药因子3(MDR3)促进磷脂分泌,通过Ⅰ期和Ⅱ期代谢酶促进胆汁酸解毒,下调胆固醇-7α-羟化酶和钠离子-牛磺胆酸共转运多肽表达,通过抑制核因子κB减轻炎症,并降低HSC中多种促纤维化基因的表达。
布地奈德是一种孕烷X受体激动剂,能够调节胆汁酸的合成、转运和代谢。目前,布地奈德主要用于具有AIH重叠征的早期PBC患者(PBC-AIH)。然而,由于存在门体分流和门静脉血栓形成导致血浆浓度升高的风险,布地奈德禁用于肝硬化或PH患者。迄今为止,免疫抑制治疗尚未改善PSC患者的预后。
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氧化酶(NOX)是活性氧的主要来源,目前已鉴定出7种NOX亚型。小鼠模型研究表明,抑制NOX可逆转胆汁淤积性纤维化。Setanaxib是一种选择性NOX1/4抑制剂。一项包括111例PBC患者的Ⅱ期临床试验显示,血清ALP和GGT水平有所改善,尤其是在基线肝硬度≥9.6 kPa且每日接受2次400 mg Setanaxib治疗的患者中。
有研究指出,TGR5激活能够诱导胆管细胞再生以维持胆道系统的完整性,并通过刺激碳酸氢盐分泌控制胆汁酸池的疏水性。在BDL和胆汁酸喂养的胆汁淤积小鼠模型中,Tgr5-/-小鼠表现出更严重的炎症和胆汁淤积性肝损伤。TGR5激动剂(如S-EMCA、INT-777)是最具代表性的半合成TGR5激动剂。然而,单独使用TGR5激动剂并不能改善Mdr2-/-小鼠的肝纤维化,而双重TGR5/FXR激动剂(如INT-767)能够减轻肝脏炎症和纤维化,这可能是通过FXR依赖性途径减少胆汁酸合成实现的。
3.2 PH管理创新
β受体阻滞剂仍是当前PH治疗基石药物,而肝窦微循环调控成为新方向。在慢性病肝脏中,一系列细胞失调会诱发肝窦的收缩状态,慢性炎症、内皮功能障碍、HSC活化等进一步扰乱肝窦环境,造成严重的结构紊乱,从而导致PH持续存在和加剧。因此,当前研究的主要重点是针对肝脏微循环功能障碍和结构扭曲(纤维化)的治疗方法。目前的指南并没有特别针对肝窦功能障碍的干预措施。Zhu等研究发现5-HT/HTR1A(5-羟色胺/5-羟色胺1A受体)轴介导门静脉平滑肌收缩,临床解痉药阿尔维林作为HTR1A拮抗剂在动物模型中显著降低门静脉压力,具有转化潜力。
4展望
近年来,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技术为疾病诊疗提供了新的工具。Mousa等开发的PSC-BAP评分系统通过整合胆汁酸谱特征,可有效预测PSC患者的肝功能失代偿事件。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有望通过多组学数据整合实现疾病精准分型、并发症预测及个体化治疗优化,但需解决数据标准化与模型可解释性等挑战。Senotherapy(衰老细胞清除疗法)在临床前研究中显示出改善疾病结局的潜力。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阐明胆管细胞衰老的驱动因素,针对衰老细胞的靶向治疗(如Senolytics)有望成为新型干预策略。此外,多项研究报道肠道菌群失调在疾病发展中起关键作用,靶向肠道菌群的干预策略(如益生菌、益生元及粪菌移植)有望成为治疗新途径。
CLD-PH的病理网络涉及多器官交互,有必要建立“胆管保护-纤维化抑制-血管重塑”三位一体治疗策略。通过整合分子机制研究、新型靶向药物开发及人工智能辅助决策,有望实现个体化精准管理,改善患者长期预后。
全文下载
https://www.lcgdbzz.org/cn/article/doi/10.12449/JCp507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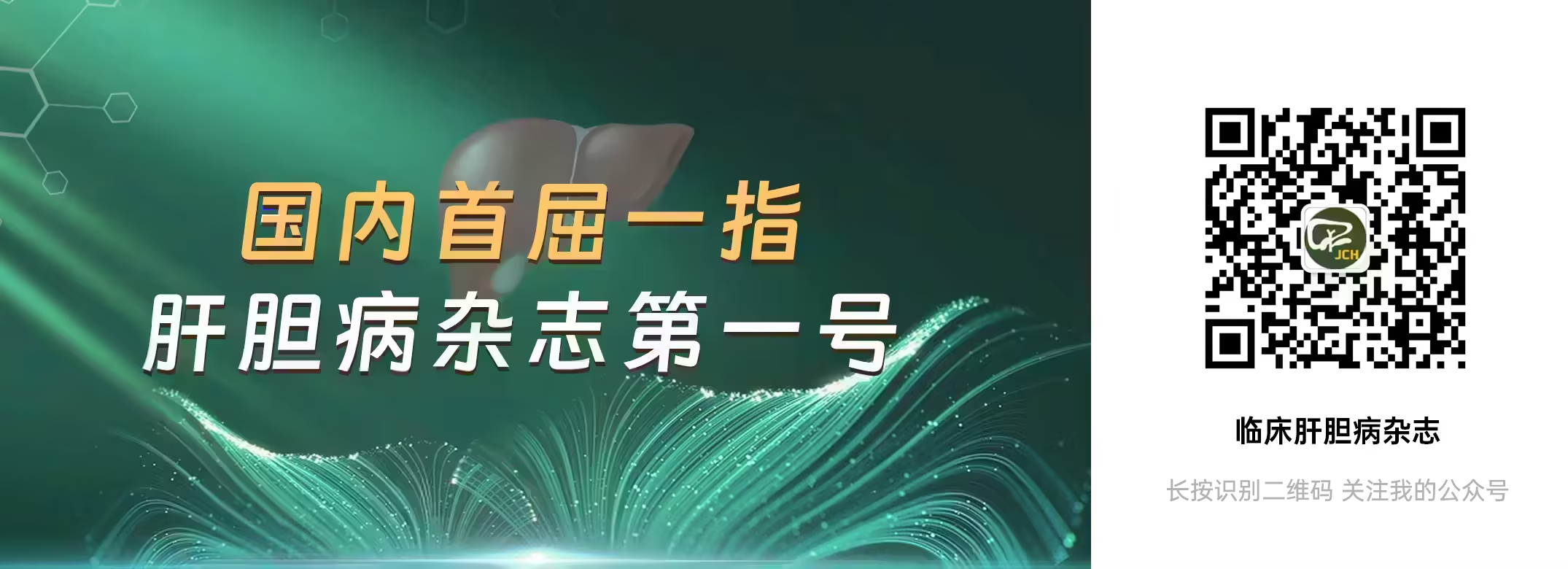
- 搜索
-
- 1000℃李寰:先心病肺动脉高压能根治吗?
- 1000℃除了吃药,骨质疏松还能如何治疗?
- 1000℃抱孩子谁不会呢?保护脊柱的抱孩子姿势了解一下
- 1000℃妇科检查有哪些项目?
- 1000℃妇科检查前应做哪些准备?
- 1000℃女性莫名烦躁—不好惹的黄体期
- 1000℃会影响患者智力的癫痫病
- 1000℃治女性盆腔炎的费用是多少?
- 标签列表
-
- 星座 (702)
- 孩子 (526)
- 恋爱 (505)
- 婴儿车 (390)
- 宝宝 (328)
- 狮子座 (313)
- 金牛座 (313)
- 摩羯座 (302)
- 白羊座 (301)
- 天蝎座 (294)
- 巨蟹座 (289)
- 双子座 (289)
- 处女座 (285)
- 天秤座 (276)
- 双鱼座 (268)
- 婴儿 (265)
- 水瓶座 (260)
- 射手座 (239)
- 不完美妈妈 (173)
- 跳槽那些事儿 (168)
- baby (140)
- 女婴 (132)
- 生肖 (129)
- 女儿 (129)
- 民警 (127)
- 狮子 (105)
- NBA (101)
- 家长 (97)
- 怀孕 (95)
- 儿童 (93)
- 交警 (89)
- 孕妇 (77)
- 儿子 (75)
- Angelababy (74)
- 父母 (74)
- 幼儿园 (73)
- 医院 (69)
- 童车 (66)
- 女子 (60)
- 郑州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