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医疗资讯/ 正文
引言
在与癌症的漫长战争中,“复发”是一个令人心碎的词语。对于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的患者而言,尽管现代医学已经能治愈大多数初诊病例,但仍有约15-20%的患儿会在治疗后经历疾病的卷土重来。这些复发的白血病细胞往往更具侵袭性,对化疗药物也产生了耐药性。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是什么让那些看似已被彻底清除的癌细胞,有机会东山再起?
长久以来,医学界一直在追寻导致复发的“幽灵”。我们知道,基因突变是癌症的根源,但驱动复发的关键突变和分子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笼罩在迷雾之中。我们迫切需要找到能够预测复发风险的“水晶球”,从而为高风险患者量身定制更强有力的治疗方案。
8月6日,《Nature》的研究报道“Excised DNA circles from V(D)J recombination promote relapsed leukaemia”,为我们揭开了一桩尘封已久的“悬案”。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一个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无害“细胞垃圾”的分子——一种名为切除信号环(Excised Signal Circles, ESCs)的环状DNA。他们发现,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DNA残片,在特定的白血病细胞中,竟扮演了“幽灵推手”的角色,悄无声息地播下复发的种子。
该研究不仅挑战了我们对免疫系统运作的传统认知,更可能彻底改变我们未来诊断和治疗白血病的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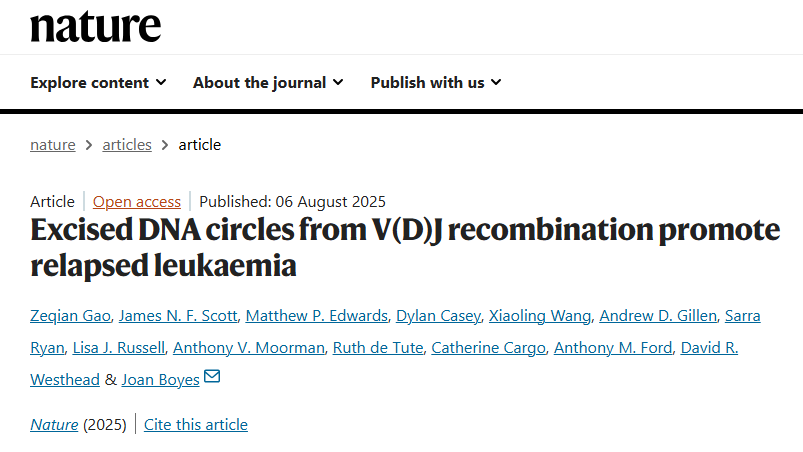
不甘沉寂的“细胞尘埃”:V(D)J重组的意外遗产
要理解这个故事,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个生命体内堪称艺术的生物学过程——V(D)J重组。我们的免疫系统之所以能识别并对抗成千上万种不同的病原体,其秘密武器在于B细胞和T细胞能产生种类繁多的抗体和T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 TCR)。这个过程就像一位技艺高超的基因“大厨”,从一个包含V(Variable,可变)、D(Diversity,多样性)和J(Joining,连接)三种“食材”的巨大基因库中,随机挑选几样进行“烹饪”和“拼接”。每一次拼接,都会创造出一份独一无二的“菜谱”,即一个独特的抗体或TCR基因。
然而,在这场基因的“创造性烹饪”中,那些未被选中的基因片段以及它们之间的间隔DNA,会被像“边角料”一样切除。这些“边角料”并不会立即被降解,而是会自我环化,形成一个稳定的闭合环状DNA分子,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切除信号环(ESCs)。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典的细胞生物学教科书告诉我们,ESCs是V(D)J重组的无害副产品。它们没有复制起点,也没有着丝粒(centromere),因此在细胞分裂时无法被平均分配到子代细胞中。理论上,随着细胞一次又一次地分裂,这些ESCs会被不断“稀释”,最终在细胞群体中消失殆尽,就像被风吹散的尘埃。基于这种“常识”,ESCs一直被认为是没有生物学功能的“惰性分子”。
然而,该研究的作者们对这个“常识”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这些“细胞尘埃”真的甘于沉寂吗?
为了验证这一点,研究人员首先在健康小鼠的B细胞中展开了分析。他们设计了一种巧妙的定量PCR方法。在ESC上,V和J基因片段的信号序列(recombination signal sequences, RSSs)被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特的“信号接头”(signal joint, SJ)。而在细胞的主染色体上,经过重组的V和J基因片段则形成一个“编码接头”(recombination junction)。研究人员精确测量了不同发育阶段B细胞中,SJ(代表ESC的数量)与编码接头(代表发生过重组的细胞数量)的比值。
如果传统认知是正确的,那么从不成熟的B细胞(pre-B细胞)发育到成熟的、经历过多次分裂的B细胞(IgG+细胞),这个比值应该会因为ESC的稀释而显著下降。然而,实验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对于几种不同的V-J重组事件,例如Jκ5-Vκ3-1和Jκ5-Vκ16-104,这个比值非但没有下降,在成熟的IgG+细胞中反而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意味着,ESC并没有如预期那样被稀释掉,它们似乎有某种机制在“抵抗”被清除的命运。
这个发现引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这些持续存在的ESC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它们是重新整合回了基因组,还是依然以独立的环状形式存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动用了一种叫做RecBCD的核酸外切酶。这种酶是一个“线性DNA杀手”,它能从DNA的末端开始,高效地降解线性的DNA分子,但对于没有末端的闭合环状DNA却束手无策。
他们从小鼠脾脏的成熟B细胞中提取了高质量的基因组DNA,然后用RecBCD酶进行处理。结果显示,作为线性基因组DNA对照的Gapdh基因,其数量在处理后下降到几乎检测不到的水平。然而,代表ESC的SJ序列,在经过处理后,仍有超过50%的量被保留了下来。这一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在经历了多次细胞分裂后,大量的ESCs依然以独立的、闭合的环状形式,顽强地存在于成熟B细胞中。
这些在健康小鼠体内的发现,已经足够颠覆传统认知。它暗示着,ESCs并非转瞬即逝的“细胞尘埃”,而可能是细胞内长期存在的“编外成员”。那么,在疾病状态下,尤其是在以V(D)J重组异常为特征的白血病中,这些“编外成员”又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从“鼠”到“人”:白血病复发迷案的追踪
B细胞前体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cell precursor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aemia, BCP-ALL)是一种起源于B淋巴细胞前体的恶性肿瘤。在这种疾病中,负责V(D)J重组的RAG蛋白(recombination-activating gene proteins)常常会“不合时宜”地被重新激活。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一群本该“退休”的基因剪刀(RAG蛋白),在一群快速增殖的癌细胞中“重操旧业”,而这些细胞里可能还漂浮着大量被忽视的环状DNA模板(ESCs)。这会是一个“完美风暴”的配方吗?
带着这个疑问,研究团队将研究重心转向了BCP-ALL的临床样本。他们建立了一种名为LAM-ESC(Linear Amplification-Mediated ESC)的超高通量测序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像雷达一样,精准地扫描并定量病人样本中每一种ESC的数量。他们分析了71名BCP-ALL患儿在初次诊断时采集的骨髓样本。这些患儿中,34人后来不幸复发,而另外37人则保持持续缓解(即未复发)。
当LAM-ESC的分析结果呈现在电脑屏幕上时,一幅惊人的画面出现了。研究人员将每个病人的ESC总拷贝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绘制了一张散点图。图中,代表复发组病人的红点和代表未复发组病人的蓝点,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群体。
数据显示,在复发组的34名患者中,有大量患者的ESC水平显著高于一个特定的阈值(这个阈值是根据健康人血样中检测到的最高ESC水平设定的)。相比之下,在未复发的37名患者中,绝大多数人的ESC水平都低于这个阈值,与健康人相当。通过严格的统计学检验,研究人员发现,诊断时拥有高水平ESC与未来的复发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其P值低至0.00017。这就像在说,初诊时细胞内ESC的数量,几乎可以被看作是预测未来是否会复发的水晶球。
当然,严谨的科学探索需要排除各种可能的干扰因素。一个自然而然的疑问是:复发组的ESC水平更高,会不会仅仅是因为他们体内的RAG蛋白活性更强,从而产生了更多的ESC?
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研究人员分析了部分病人样本中RAG1和RAG2基因的表达水平。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发现ESC的拷贝数与RAG基因的表达水平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线性关系。更有说服力的是,他们筛选出了一组RAG1表达水平非常相似的患者,再次比较了他们的ESC水平。结果,即便在RAG基因表达量几乎相同的情况下,那些后来复发的患者,其ESC拷贝数依然显著高于未复发的患者(P = 0.0156)。
这个对照实验有力地排除了“RAG表达量高导致ESC多”这一简单解释。它强烈地暗示,复发倾向的白血病细胞中存在着某种超越RAG表达水平本身的、内在的生物学特性,这种特性要么导致了ESC的异常积累,要么是ESC本身在其中扮演了更主动的角色。无论如何,谜团的核心似乎正指向ESC本身。这些“细胞尘埃”,绝非无辜的旁观者。
幽灵的秘密:流氓环状DNA的自我复制
ESC数量与复发风险之间的惊人关联,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个根本问题:如果ESC不能自我复制,它们是如何在快速分裂的癌细胞中维持如此高的拷贝数的?唯一的合理解释是:这些ESC一定在进行自我复制!
这个猜想虽然大胆,但却直指问题的核心。为了验证它,研究团队又一次展现了他们巧妙的实验设计思路。他们利用了V(D)J重组的一个特点:每当一个ESC被切除并形成时,它都会在主染色体上留下一个与之对应的、独一无二的“足迹”——编码接头。
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如果一个ESC是“最近”才生成的,那么细胞里应该只有一个编码接头“足迹”。如果一个ESC是在“很久以前”生成的,那么随着细胞的多次分裂,这个“足迹”也会被复制多次,细胞里就会有许多个同样的“足迹”。现在,如果ESC本身也能复制,那么即便对于那些“最近”生成的ESC(只有一个“足迹”),我们也应该能检测到多个ESC拷贝。
基于这个逻辑,研究人员专注于那些在病人样本中信号最弱、也就是最可能是“最近”生成的ESC。他们比较了这些“新鲜出炉”的ESC的拷贝数(通过SJ定量)和它们对应的染色体“足迹”的数量(通过编码接头定量)。
结果再次为他们的猜想提供了坚实证据。在那些未来会复发的患者中,这些“新”ESC的数量与它们“足迹”数量的比值,显著高于那些未复发的患者(P = 0.004)。这证明,在复发倾向的白血病细胞中,ESC的复制活动异常活跃。这些环状DNA并非被动地等待稀释,而是在主动地、高效地“传宗接代”。
是什么内在因素驱动了ESC的疯狂复制呢?为了寻找线索,研究人员转向了基因表达谱的分析。他们利用公共数据库中123名BCP-ALL患者的RNA测序数据(其中74人复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基因集富集分析(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 GSEA)。他们发现,在那些注定要复发的患者样本中,与“DNA修复”(DNA REPAIR)相关的基因集被显著上调(P = 0.0095)。
随后,他们又在自己的病人样本中,利用RT-qPCR技术验证了几个关键的、与DNA复制和修复相关的基因,如PCNA、POLE3、POLE4和RBX1。结果证实,在那些ESC水平高的复发患者中,这些基因的表达量确实显著高于ESC水平低的患者。
至此,一幅清晰的分子图景开始浮现:在那些具有复发倾向的白血病细胞中,存在一种“细胞内在”(cell-intrinsic)的异常状态。这种状态表现为DNA复制和修复系统的过度活跃,它不仅为癌细胞的生长提供了便利,似乎也无意中为ESC的复制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本应被清除的“边角料”,在这种纵容的环境下,得以大量复制,最终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潜伏在细胞核内的“幽灵军团”。
现在,这支军团已经集结完毕。下一步,它们将会做什么?
犯罪现场:揭开基因突变的层层迷雾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复发高风险的BCP-ALL细胞中,同时存在着两大“危险分子”:1)重新被激活的基因剪刀——RAG蛋白;2)数量庞大且能自我复制的环状DNA——ESCs。当这两者相遇,会擦出怎样致命的“火花”?
以往的研究已经揭示,RAG-ESC复合物有一种独特的破坏能力,被称为“切跑”(cut-and-run)机制。在这个过程中,RAG蛋白会与ESC结合,形成一个不稳定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像一个失控的“基因巡航导弹”,它不再规规矩矩地待在免疫球蛋白基因座上,而是会在整个基因组中游荡。当它在基因组的其他位置遇到与V(D)J重组信号序列(RSSs)相似的序列时——这种序列被称为“隐匿性RSS”(cryptic RSS, cRSS)——它就会在那里进行一次错误的“切割”。
这种切割的特点是,它只在cRSS的一侧造成DNA双链断裂(double strand break, DSB),而另一侧的基因组则完好无损。这种“单边”的断裂非常容易在修复时出错,从而导致基因的缺失、插入或易位等结构变异(structural variants, SVs)。因此,“单边cRSS断点”就成了RAG-ESC复合物作案后留下的独特“犯罪签名”。
如果RAG-ESC复合物真的是导致复发的元凶,那么在复发患者的基因组中,我们应该能找到更多这样的“犯罪特征”。
研究团队利用一个大型公共数据库(TARGET),分析了150名BCP-ALL患者(121名复发,29名未复发)在诊断时的全基因组测序数据。他们仔细地检查了每一个基因结构变异的断点,看它周围是否存在cRSS。
分析结果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与未复发组相比,复发组患者的基因组中,含有“单边cRSS”的结构变异数量显著更高(P = 0.016)。这直接将ESC介导的“切跑”式基因损伤机制与白血病的复发倾向联系了起来。
分析并未就此止步。研究人员进一步追问:这些由ESC引发的基因突变,是随机分布的,还是有特定的攻击目标?他们将目光锁定在了一组已知的、在BCP-ALL复发过程中经常发生突变的“复发相关基因”上,例如IKZF1, CREBBP, NT5C2等。
当他们将分析聚焦于这些关键基因时,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数据显示,在这些“复发相关基因”区域内发生的“单边cRSS”突变事件,其频率远高于基因组的平均水平(P = 0.0001)。这不再是随机的破坏,而是精准的“定点打击”。RAG-ESC这枚“巡航导弹”,似乎有选择性地轰炸了那些能够帮助癌细胞逃避化疗、促进其生存和增殖的“关键堡垒”。
为了建立更直接的因果链,研究人员将病人按照RAG1表达水平和ESC水平分成了不同组别。他们发现,在“RAG1高表达”且“ESC高水平”的这一组病人中,“单边cRSS”突变在复发相关基因中的富集程度达到了顶峰(P = 9.44e-07)。而在RAG1表达低或ESC水平低的组别中,这种现象则不明显。
这最后一击,几乎锁定了RAG-ESC复合物的“罪行”。它清晰地描绘了从分子到临床的完整逻辑链:高水平的ESC与高活性的RAG蛋白狼狈为奸,通过“切跑”机制,在与复发密切相关的基因上制造了大量突变,这些突变赋予了白血病细胞更强的生存优势,最终导致了化疗失败和疾病复发。
至此,这起潜伏多年的“细胞悬案”,终于真相大白。
旧敌新解:重塑白血病复发的认知版图
这项里程碑式的研究,为我们理解白血病复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式。它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细胞副产品——ESC,从“无辜的旁观者”推上了“核心案犯”的席位。
现在,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关于BCP-ALL复发的新模型:
在那些倾向于复发的患者体内,一场恶性循环正在上演。异常活跃的RAG蛋白,不仅驱动了白血病的发生,也持续产生着新的ESC。同时,这些癌细胞内部的某些未知因素(可能与DNA复制/修复系统的过度活化有关),为ESC的自我复制提供了“温床”,导致ESC数量急剧累积。这些海量的ESC与RAG蛋白结合,形成了一个持续制造基因突变的“工厂”。这个工厂不断地攻击着那些对癌细胞生存至关重要的基因,日积月累,最终筛选出了一批对化疗药物刀枪不入、生命力极其顽强的“超级癌细胞”。这些细胞在初次治疗的狂轰滥炸中得以幸存,并最终发展壮大,导致了疾病的复发。
相比之下,在那些不太可能复发的患者体内,虽然也会产生ESC,但由于缺乏高效的复制机制,它们的数量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因此,RAG-ESC复合物能够造成的基因损伤是有限的,癌细胞的“进化”速度较慢,更容易被标准化疗方案所清除,从而实现长期治愈。
这一新模型的建立,其意义远不止于满足我们的科学好奇心。它为临床实践带来了切实的希望。既然诊断时的高ESC水平与未来的高复发风险密切相关,那么检测ESC的拷贝数,完全有潜力成为一种全新的、强有力的预后生物标志物(biomarker)。
我们可以设想未来的临床场景:每一位新诊断的BCP-ALL患儿,除了进行常规的检查外,还会进行一次骨髓样本的ESC水平检测。医生可以根据ESC的“读数”,将患者精确地分层为“高危复发组”和“低危复发组”。对于低危患者,可以继续采用标准的、毒副作用相对较小的治疗方案;而对于那些ESC水平极高的高危患者,则可以在治疗之初就果断采取更激进的策略,例如加大化疗强度、引入靶向药物,甚至是更早地考虑造血干细胞移植,从而将复发的风险扼杀在摇篮之中。
当然,从基础研究的突破到临床应用的普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来验证这一生物标志物的普适性和准确性,也需要开发出更快速、更经济的ESC检测方法。但无论如何,该研究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它让我们看到,在看似混乱无序的癌细胞世界里,隐藏着精密的、可以被我们理解和利用的规律。
这个关于“流氓DNA环”的故事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生命的复杂系统中,不存在真正的“垃圾”。每一个被我们忽视的角落,都可能隐藏着决定命运的关键线索。对科学的探索,正是这样一场永无止境的、在“未知”与“已知”之间追逐的伟大冒险。而这一次,我们似乎离照亮白血病患儿未来的那束光,又近了一步。
参考文献
Gao Z, Scott JNF, Edwards MP, Casey D, Wang X, Gillen AD, Ryan S, Russell LJ, Moorman AV, de Tute R, Cargo C, Ford AM, Westhead DR, Boyes J. Excised DNA circles from V(D)J recombination promote relapsed leukaemia. Nature. 2025 Aug 6. doi: 10.1038/s41586-025-09372-6.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0770098.
猜你喜欢
- 让老人都能安心养老,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 夫妻不和谐女性有责任 男女别太粘婚姻易长久
- 2018年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健康心理,快乐人生”——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 改善孕妇在怀孕期间出现贫血情况的食疗粥做法
- GW-ICC/AHS.25 | 腔内影像学"金标准"时代,如何精准导航左主干PCI?
- 每天做20个深蹲有什么好处 深蹲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 深度剖析一例新辅助治疗方案联合手术治疗食管癌的临床疗效
- Cardiovasc Diabetol: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肾功能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
- Nat Commun 华东师范大学钟涛研究团队揭示线粒体氧化呼吸与心脏能量代谢调控新机制
- 高血压病人的用药注意事项以及用药指导
- 搜索
-
- 1000℃李寰:先心病肺动脉高压能根治吗?
- 1000℃除了吃药,骨质疏松还能如何治疗?
- 1000℃抱孩子谁不会呢?保护脊柱的抱孩子姿势了解一下
- 1000℃妇科检查有哪些项目?
- 1000℃妇科检查前应做哪些准备?
- 1000℃女性莫名烦躁—不好惹的黄体期
- 1000℃会影响患者智力的癫痫病
- 1000℃治女性盆腔炎的费用是多少?
- 标签列表
-
- 星座 (702)
- 孩子 (526)
- 恋爱 (505)
- 婴儿车 (390)
- 宝宝 (328)
- 狮子座 (313)
- 金牛座 (313)
- 摩羯座 (302)
- 白羊座 (301)
- 天蝎座 (294)
- 巨蟹座 (289)
- 双子座 (289)
- 处女座 (285)
- 天秤座 (276)
- 双鱼座 (268)
- 婴儿 (265)
- 水瓶座 (260)
- 射手座 (239)
- 不完美妈妈 (173)
- 跳槽那些事儿 (168)
- baby (140)
- 女婴 (132)
- 生肖 (129)
- 女儿 (129)
- 民警 (127)
- 狮子 (105)
- NBA (101)
- 家长 (97)
- 怀孕 (95)
- 儿童 (93)
- 交警 (89)
- 孕妇 (77)
- 儿子 (75)
- Angelababy (74)
- 父母 (74)
- 幼儿园 (73)
- 医院 (69)
- 童车 (66)
- 女子 (60)
- 郑州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