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医疗资讯/ 正文
人类口腔微生物群种类繁多,定植着以细菌为主的多种微生物,与宿主微环境共同构成了独特的微生态系统。生理状态下,口腔菌群通过与宿主免疫系统协同作用,维持微生态平衡并阻止病原体入侵,是机体免疫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开放的生态系统,口腔菌群丰度及多样性的变化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局部健康,亦可通过炎症反应、免疫系统失调、细菌移位以及代谢产物扩散等途径间接影响包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在内的多种全身性疾病,其变化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宿主的健康状态。作为消化道的“门户”,口腔与其他消化器官之间存在天然联系,并可在多个层面进行互动。
近年来,关于口腔菌群与消化系统疾病(如炎症性肠病、胃癌、肠易激综合征)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并在部分疾病的诊断、治疗、预后评估中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例如,口腔菌群作为结直肠癌诊断的生物标志物表现出色;靶向清除具核梭杆菌可逆转化疗耐药性并增强药物疗效。研究还发现,根除口腔幽门螺杆菌(Hp)不仅有助于清除胃内菌群,还可降低复发风险;虽然13C或14C-尿素呼气试验是检测Hp感染的首选方法,但无法检测口腔中的Hp,而Hp唾液测定可快速评估口腔感染情况。这为探索口腔菌群与胰腺疾病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也为相关诊断和治疗手段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1口腔菌群概述
人类自出生起便与口腔菌群建立共生关系,随着高通量扩增子测序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人类微生物计划项目已收录了700余种细菌,使其成为仅次于肠道的第二大微生物群。微生物以浮游生物的形式悬浮在唾液中,或附着于口腔表面形成牙菌斑生物膜。由于口腔不同区域理化特性(如pH值、氧气浓度、唾液流动性等)各异,菌群丰度和多样性在空间分布上呈梯度变化:牙菌斑最高,其次是唾液,而颊黏膜相对较低。此外,健康个体的口腔菌群结构和多样性在人口学特征、个体行为习惯、社会及自然环境等多重因素塑造下呈现个体化差异。尽管口腔微环境复杂,口腔菌群仍展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与生态稳定性。
1.1 口腔核心菌群的组成及意义
研究者将健康人群口腔中常见且稳定存在的细菌定义为“口腔核心细菌群落”。这些核心细菌不仅在个体间普遍存在,还在维持口腔微生态平衡、调节宿主免疫功能等生物学或生态功能中起着关键作用。核心细菌群落的稳定性使其成为健康口腔微生物组的基本组成部分,同时适度的变异性赋予了其应对环境压力和宿主条件变化的能力。核心菌群的存在导致健康人群的口腔菌群β多样性较低,即不同个体间的菌群种类相似,这些特征为检测疾病状态下的菌群变化提供了基准,并为微生物群失调的识别和疾病的早期诊断奠定基础。
1.2 口腔菌群的稳定性及意义
口腔菌群在外界环境波动下表现出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具有一定的“弹性”。这意味着,其在受到外界干扰后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微生物组成,并在干扰解除后快速恢复平衡。Lazarevic等比较了5例健康成人在3个时间点的唾液微生物群落,发现口腔菌群在短期内(至少5天)几乎没有显著变化。另有研究表明,单一抗生素治疗对肠道和口腔微生物群的影响存在差异: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和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并伴随抗生素耐药性的富集,而唾液微生物群却表现出意外的稳定性。肠道微生物组的不稳定性增加了在某些情况下辨别微生物组变化的原因及其与健康或疾病的相关性的难度,而口腔菌群的“弹性”使其在动态环境中能更好地维持功能完整性,若这种平衡被打破或弹性显著降低,可能预示疾病发生或微生态失调。因此,口腔菌群的变化为寻找潜在生物标志物或微生态疗法靶点提供线索。
2口腔菌群与胰腺“对话”机制
口腔菌群紊乱对胰腺的致病作用仍在探索阶段,其因果关系尚未得到证实。结合目前对“口-肠轴”及“肠-胰轴”的认识,以下几种假说可以部分解释微生物从口腔迁移到胰腺的途径和潜在机制。
2.1 微生物迁移及定植
口腔与胰腺之间有直接的物理联系,口腔微生物可随吞咽动作进入胃肠道,通过开口于十二指肠的胰管迁移至胰腺。一项实验研究表明,与未灌胃组相比,牙龈卟啉单胞菌在灌胃的实验小鼠胰腺和粪便中均有沉积,为微生物迁移提供了实验证据。此外,来自以色列的一项研究追踪到了牙龈卟啉单胞菌从口腔中迁移到小鼠胰腺,并可在人体胰腺上皮内瘤变病灶中检测到,进一步证实了“口腔-肠道-胰腺”易位途径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牙周炎致病菌可以通过牙周入血进入体循环从而作用于全身。鉴于口腔高度血管化的特点,且胰腺亦是富血供器官,微生物还可能通过血液途径参与胰腺疾病的发生发展,但该机制仍有待更多研究加以证实。
2.2 毒素及代谢产物的调控作用
口腔菌群在循环系统和消化道的搭载下,其产生的代谢产物及毒力因子可以帮助他们侵入宿主细胞,诱导氧化应激和组织损伤等反应,目前研究较多的是放线菌、具核梭菌和牙龈卟啉单胞菌。放线菌可以分泌磷脂酶C破坏细胞膜结构,并释放多种毒素,常见的有白细胞毒素A、细胞致死膨胀毒素和细胞毒素相关基因E,通过多种作用机制造成细胞死亡。具核梭菌分泌的黏附素A是其最具特征的毒力因子,能与宿主细胞E-钙黏蛋白和VE-钙黏蛋白结合,激活Wnt/β-catenin信号通路,调控细胞增殖基因表达,并增加血管内皮通透性,从而在细胞侵袭、感染传播和免疫逃逸中发挥重要作用。牙龈卟啉单胞菌分泌的核苷二磷酸激酶不仅可以作为ATP酶,降低ATP浓度,抑制ATP依赖的细胞凋亡;亦可激活JAK/PI3K/Akt和JAK/STAT3等信号通路调控相关蛋白,抗凋亡蛋白Bcl-2(B细胞淋巴瘤-2)和Bcl-xL(B细胞超大淋巴瘤蛋白)上调,促凋亡蛋白Bax(Bcl-2相关X蛋白)下调,部分阻断线粒体依赖的细胞凋亡。Ikezawa等发现90%的胰腺导管腺癌中存在Bcl-xL过表达。
2.3 炎症反应与免疫失调
细菌感染可促进炎症微环境的形成、干扰宿主免疫功能,对胰腺健康产生潜在影响。Nouri等的病例对照研究中,口腔微生物群组成的改变可能导致短链脂肪酸和游离脂肪酸受体2表达的减少,这种改变可能通过上调TNFAIP8(肿瘤坏死因子-2诱导蛋白)和IL-6/STAT3信号通路转录水平引发炎症反应,从而增加癌症发生的风险。牙龈卟啉单胞菌不仅通过释放多种毒力因子直接影响细胞信号传导,导致炎症反应加剧,还能够提高中性粒细胞趋化因子的表达,促进中性粒细胞弹性酶的分泌,进一步形成持续的促炎环境并抑制抗肿瘤免疫。具核梭菌通过与Fap2(具核梭菌黏附蛋白2)蛋白相互作用,保护肿瘤细胞免受自然杀伤细胞介导的杀伤,从而形成免疫抑制状态。
2.4 肠道菌群的协同作用
“口-肠轴”是人类健康的一个关键维度。传统观点认为,口腔微生物群数量固然庞大,但在消化液的作用下难以到达肠道。然而,根据人类微生物组计划高通量测序分析发现,所有受试者的口腔和粪便样本中均存在鞭毛藻科和韦荣球菌科的细菌,表明消化道各部位的微生物群存在大量重叠,重合率高达45%,提示口腔菌群可能通过复杂的微生态网络参与远端消化道菌群的塑造。当口腔微生物迁移至肠道时,部分菌群从兼性厌氧转变为严格厌氧,代谢方式发生显著变化。这些变化打破原有的肠道微生态平衡,导致特定条件致病菌的增加和有益菌的减少,损害肠道屏障完整性并改变肠道局部微环境。例如,发生AP时,口腔共生菌孪生球菌(Gemella)减少,而其在结肠中产生的短链脂肪酸是肠道免疫调节的重要介质,通过抑制促炎因子的产生来维持肠道屏障功能。因此,口腔菌群紊乱可能通过削弱肠道屏障功能,诱发或加重系统性炎症,间接影响胰腺健康,参与胰腺疾病的发生与发展。
3口腔菌群与胰腺疾病
胰腺是人体的第二大消化腺,涉及多种疾病类型,包括炎症性疾病、肿瘤性疾病、先天性疾病、损伤性疾病和囊性病变。既往认为胰腺是一个相对无菌的器官,但在病理状态下,病原微生物可通过血液、淋巴以及十二指肠-胰反流等途径抵达胰腺,引发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改变。
3.1 口腔菌群与胰腺癌
胰腺癌因其临床特点被誉为“癌中之王”。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胰腺癌患者的口腔、肠道和胰周组织微生物与正常人不同,并与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提示微生物可作为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和预测因子,为胰腺癌的诊治提供新视角。
多项前瞻性研究表明,牙周疾病与胰腺癌发病风险增加有关。后续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口腔菌群的失衡与胰腺癌关系密切,牙周病细菌标志物和微生物分类群多样性的变化具有作为胰腺癌非侵入性筛查生物标志物的潜力。Farrell等比较了胰腺癌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的唾液微生物,发现两组间菌群结构存在显著差异;进行细菌生物标志物的鉴定和独立验证,发现胰腺癌患者的唾液中长奈瑟菌(Neisseria elongata)和缓症链球菌(Streptococcus mitis)水平显著降低,而毗邻颗粒链菌属(Granulicatella adiacens)水平显著升高,基于Neisseria elongata和Streptococcus mitis的差异研究构建了诊断胰腺癌的模型,其敏感度为96.4%,特异度为82.1%。另一项横断研究发现,胰腺癌患者和其他患者群体之间最显著的微生物特征差异是细菌属细毛菌和卟啉单胞菌的比值(LP比值)。学者成功地使用LP比值对1例初诊未诊断为胰腺癌、但高LP比值的患者进行了重新分类,该患者被重新评估并诊断为胰腺癌,进一步支持LP比值可能作为胰腺癌生物标志物的观点。研究口腔菌群的特定变化对肿瘤危险人群筛查及肿瘤的早期检测具有重大意义。
口腔微生物群在健康、共生状态下对胰腺癌具有保护作用,但在病理状态下可能促进恶性肿瘤的发生和发展。Michaud等发现,口腔细菌抗体水平与胰腺癌风险的关联。对405例胰腺癌患者和416例匹配对照的诊断前血液样本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高滴度牙龈卟啉单胞菌抗体的患者胰腺癌发病风险增加两倍;针对非致病性共生细菌的高抗体滴度则显著降低了胰腺癌风险(降低45%)。Fan等研究发现关键菌种的风险差异:牙龈卟啉单胞菌和放线菌均与胰腺癌患病风险的增加相关(OR=1.6,95%CI:1.15~2.22);相反,梭杆菌(Fusobacterium)和纤毛菌(Leptotrichia)的存在与胰腺癌患病风险降低相关。Trikudanathan等研究指出,Hp可通过引发胃溃疡导致胃酸分泌减少,进而升高个体亚硝胺水平,这种改变可能促进口腔中牙龈卟啉单胞菌的过度生长,进一步加剧胰腺癌的快速进展;血清IgG抗体阳性患者患胰腺癌的风险会增加38%(OR=1.38,95%CI:1.08~1.75),这提示Hp可能在胰腺癌的发生发展中起作用。这些研究为口腔微生物组作为预测胰腺癌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提供了有力证据。
3.2 口腔菌群与急、慢性胰腺炎
急性胰腺炎(AP)是常见的急腹症之一。针对AP严重程度的评分系统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局限性,故迫切需要更加准确可靠的生物标志物,以支持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到AP期间口腔菌群的变化,但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Liu等首次从物种多样性、微生物群落组成、诊断预测模型、功能预测模型、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5个方面描述了AP患者口腔微生物群的特征。研究发现,AP患者口腔微生物的相对丰度和多样性增加,而肠道微生物群的相对丰度和多样性则呈现下降趋势。有观点认为,口腔微生物群多样性的增加往往预示着炎症和疾病。基于23个关键物种构建诊断预测模型,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为0.80(95%CI:0.72~0.87),表现出较高的诊断准确性;Lefte分析表明,普雷沃菌、胃链球菌、放线菌和卟啉单胞菌鉴定为潜在标志物,这些结果为疾病的早期诊断打开了思路。此外,口腔微生物组成可能会影响AP的严重程度。中度重症AP和重症AP中的口腔微生物组成与轻症AP有显著差异,表现为有益菌的减少和机会致病菌的增加,提示口腔菌群可能是疾病严重程度的早期预测因子。最近的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队列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AP患者的口腔和肠道微生物组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及临床特征密切相关,通过构建包含16个微生物和系统性炎症反应综合征的分类器,可以预测疾病严重程度,其预测准确率高达93.9%,优于现有的严重程度评分标准。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口腔微生物群不仅可以作为AP的诊断标志物,还有助于优化治疗决策并改善患者预后。
此外,近期研究表明,唾液微生物群的变化可能与慢性胰腺炎(CP)的发生和进展密切相关。普雷沃菌科是口腔微生物组中的核心厌氧性菌群之一,在CP患者中表现出较高的丰度。与其他口腔共生菌相比,普雷沃菌具有更强的诱导炎症介质的能力,其通过激活Toll样受体2,诱导炎症介质如IL-8和IL-6的释放,从而增强炎症反应,因此认为其可能通过促进慢性炎症参与CP的发生与进展。然而,关于这种关联的具体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特别是需要大规模纵向研究来验证其在CP中的作用及临床意义。
3.3 口腔菌群与其他胰腺疾病
术后胰瘘(POPF)是胰腺手术后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近期一项前瞻性研究探讨了口腔菌群在预测术后胰瘘中的潜力。该研究通过分析4种丰度差异显著的菌群(副流感嗜血杆菌、血芽孢杆菌、溶血链球菌和戈多链球菌),并结合身体质量指数建立了预测模型,该模型的AUC达到了93.9%,说明术前口腔菌群的组成与POPF的发生显著相关。这为胰腺手术前制订个性化预防性抗菌策略提供了依据,尤其在肥胖患者中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AIP)是一种由自身免疫介导的CP,伴随胰腺组织浸润大量炎性细胞和纤维化。在非胃炎患者的牙菌斑中检测到Hp,提示口腔为其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是除胃以外的重要储存库。研究表明,Hp可能通过分子模拟效应参与AIP的发病。Guarneri等发现Hp表达的α-碳酸酐酶与胰管上皮细胞产生的人类碳酸酐酶Ⅱ高度同源;而后,Frulloni等进一步描述了Hp纤溶酶原结合蛋白,其在分子水平上与胰腺腺泡细胞表达的泛素-蛋白连接酶E3组分N-recognin 2相似,且高达95%的AIP患者对纤溶酶原结合蛋白呈抗体阳性,而其他胰腺疾病(如慢性酒精性胰腺炎)未见此现象,因此,Hp感染可能是AIP的潜在诱因之一,但这一推测尚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囊性纤维化是一种由CFTR(囊性纤维化跨膜传导调节因子)基因突变引起的遗传性疾病,涉及多器官系统,累及胰腺的情况并不少见,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是最常见的胰腺受累形式。有研究认为,唾液菌群或可预测囊性纤维化的疾病进展。存在于囊性纤维化患者口腔中的铜绿假单胞菌,其代谢产物引起的慢性炎症可以诱导单核细胞和内皮细胞上黏附分子的表达,这有助于内皮细胞招募单核细胞到血管壁和易位到内皮下,与黏膜纤维化的发生密切相关。
4小结与展望
全球对人体微生物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肠道领域,而口腔微生物组学的研究相对滞后,直到1960年,龋齿才被确认为可能由变形链球菌引起的传染性疾病。这一发现虽开启了口腔菌群致病机制研究的序章,但相比肠道微生物组学的飞速发展,口腔微生物组学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仍存在明显差距。其滞后性可能源于以下原因:对口腔微生物群复杂性认识不足,以及对其潜在临床应用价值关注不足等。
近年来,口腔微生物组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具体机制尚需深入探索。当前研究已表明,口腔菌群不仅影响局部疾病如龋齿和牙周炎,还通过菌群迁移、免疫调控和代谢途径干预全身性疾病的发生与进展。然而,针对口腔菌群与胰腺疾病关系的研究仍较为有限,口腔微生态的失衡和口腔微生物的异常定植,究竟是胰腺疾病的原因还是结果难以捉摸,具体致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亟需更多高质量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提供证据。
未来,加大对口腔微生物组的研究投入,尤其是其在局部与系统性疾病中的作用机制,将有助于拓展微生态学的整体认识。新兴技术如多组学整合分析、高通量测序及人工智能算法的应用,将为揭示口腔菌群与胰腺疾病的复杂关系提供更有力的工具。此外,多中心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和疾病特异性菌群标志物的鉴定,将推动口腔微生物组在疾病早期诊断、精准治疗及预后评估中的转化应用,进一步彰显其在临床医学中的潜力。
全文下载
https://www.lcgdbzz.org/cn/article/doi/10.12449/JCH2508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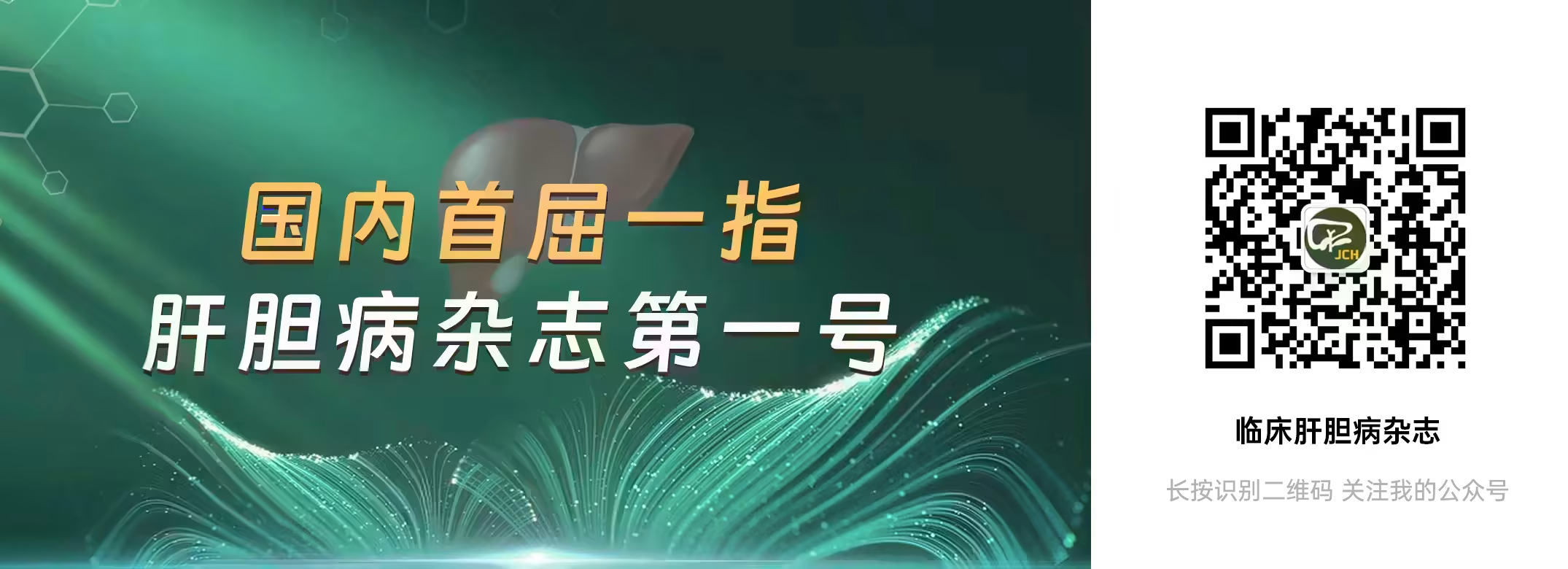
猜你喜欢
- 练腹肌三餐吃啥最好是 练腹肌不能吃什么食物
- Head Neck Pathol:与PIK3CA和HRAS突变相关的上颌龈透明细胞鳞状细胞癌:1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 Critical Care Medicine:基于膈肌努力滴定吸气支持的肺和膈肌保护性通气
- 包皮过长导致阳痿和影响阴茎长度
- 「对话·心内」ESH专访刘丰教授:新欧洲高血压指南要点讲解,多数患者血压应降至130/80mmHg!
- 复课学生超过1亿 复课学生应当做些哪些
- 【CSCO 2022前瞻】|MSI在胃肠肿瘤临床应用及新进展
- 触诊 | 大菱形肌,后锯肌,竖脊肌
- 什么时候上环最好 上环避孕要知道的4个注意事项
- Redox Biol:人类和小鼠炎症巨噬细胞对血红素的独特代谢反应—一氧化氮的作用
- 搜索
-
- 1000℃李寰:先心病肺动脉高压能根治吗?
- 1000℃除了吃药,骨质疏松还能如何治疗?
- 1000℃抱孩子谁不会呢?保护脊柱的抱孩子姿势了解一下
- 1000℃妇科检查有哪些项目?
- 1000℃妇科检查前应做哪些准备?
- 1000℃女性莫名烦躁—不好惹的黄体期
- 1000℃会影响患者智力的癫痫病
- 1000℃治女性盆腔炎的费用是多少?
- 标签列表
-
- 星座 (702)
- 孩子 (526)
- 恋爱 (505)
- 婴儿车 (390)
- 宝宝 (328)
- 狮子座 (313)
- 金牛座 (313)
- 摩羯座 (302)
- 白羊座 (301)
- 天蝎座 (294)
- 巨蟹座 (289)
- 双子座 (289)
- 处女座 (285)
- 天秤座 (276)
- 双鱼座 (268)
- 婴儿 (265)
- 水瓶座 (260)
- 射手座 (239)
- 不完美妈妈 (173)
- 跳槽那些事儿 (168)
- baby (140)
- 女婴 (132)
- 生肖 (129)
- 女儿 (129)
- 民警 (127)
- 狮子 (105)
- NBA (101)
- 家长 (97)
- 怀孕 (95)
- 儿童 (93)
- 交警 (89)
- 孕妇 (77)
- 儿子 (75)
- Angelababy (74)
- 父母 (74)
- 幼儿园 (73)
- 医院 (69)
- 童车 (66)
- 女子 (60)
- 郑州 (58)